带领中国进入世界天文俱乐部的北京大学教授何子善
何志平,48岁,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 作为一名在中国工作两年多的美国研究员,他对中国的科学野心有着独特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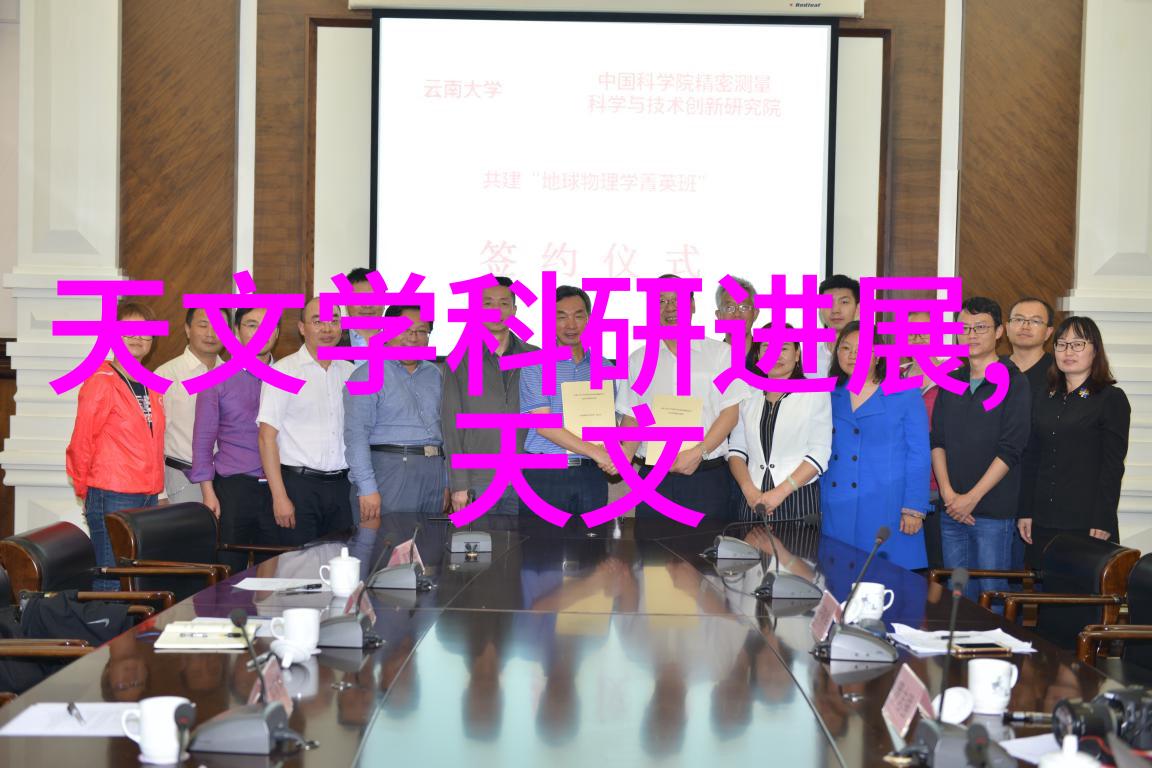
贺子善
贺子善在加州帕萨迪纳的卡内基天文台工作,目前正在休假。 今年夏天,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也是埃德温·P·哈勃的办公室)聊了近三个小时,后来又通了电话。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摘要版本。
记者:你在哪里长大?
贺子善:我在莫桑比克长大,当时莫桑比克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在我童年的非洲,存在着关于出身的冲突。 葡萄牙人对我们不太欢迎,而且有很多种族主义的外在表现。 然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那个国家独立并不可避免地陷入丑陋的内战后,我们被迫离开。 他们没收了我父亲的所有财产,我们带着手提箱离开了。
记者:你去哪儿了?
贺子山:因为运气好,我们好歹拿到了美国签证,所以就去了东波士顿。 我当时 12 岁,是一所非常糟糕的学校里唯一的亚洲学生。 我父亲在一家餐馆洗碗。 在学校里,人们取笑我。 这让我下定决心要尽快学好英语,这样我就可以去更好的学校。 我做到了。 我去了这个城市最好的学校,波士顿拉丁学校。 从那里我去了哈佛; 在那里,我似乎是唯一一个不富有却必须工作的人。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
记者:这种情况什么时候结束?
贺子善:有一天,我碰巧在哈佛大学参加一场关于银河系黑洞的讲座。 我完全被迷住了。 我找到了演讲者 Paul Ho,他立即给了我一个研究项目。
我喜欢天文学的众多原因之一是它与世俗世界无关。 它甚至与我们的星球没有任何关系。 也许,这是对我的家人必须处理的所有日常琐事的反应。
记者:您从事什么天文学领域?
贺子山:黑洞。 我是最早证明黑洞实际上很常见的人之一。 这是我 1995 年博士论文的结论之一。 在那之前,人们认为黑洞应该存在,但没有证据。 我证明了每个大星系都有一个包含超大质量黑洞的核心。 以前人们只是怀疑,但我证明了这一点。
记者:你是怎么做到的?
贺子山:想办法间接的证明它的存在。 我寻找能量的迹象,我发现几乎每个星系都有一个黑洞,但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它。
我完成博士学位后,哈勃太空望远镜被修复了。 我可以利用它的观测数据来测量这些黑洞周围恒星和气体的旋转速度。 哈勃证实了我论文中的许多想法。
记者:黑洞对于了解宇宙的面貌有什么意义?
贺子山:根据我们目前的情况,黑洞应该被认为是每个星系呈现出现在样子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个大问题是,像黑洞这样小的东西如何影响整个星系本身? 目前相信它们可以相互作用。
记者:我们生活在一个宇宙知识取得巨大突破的时代。 为什么我们现在知道这么多?
贺子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的推动。 天文学家拥有很多很棒的新设备。 天文学的快速发展完全归功于大型天文望远镜的使用。 这也是我敦促中国领导人参与新型大型国际天文望远镜建设的原因之一。
中国在科学上有远大的抱负。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要加入天文俱乐部,你需要参与大型天文望远镜的建造。 要让他们相信这三台新望远镜都在外国土地上并不容易,这让他们难以接受。 他们最终选择与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加拿大和印度合作建造三十米望远镜。
记者: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想过将来在中国生活和工作?
贺子山:没想过。 有很多事情影响了我,其中之一就是结识了许多才华横溢的中国年轻科学家。 我帮助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了美国的大学。 他们在美国的挣扎让我同情他们。 当他们回到中国时,他们并不总是成功,他们的才华和机会也不匹配。
在过去的十年里,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在科学上投入巨大,这些人回来后有事可做。 当 Kavli 的人们在 2013 年联系我时,我觉得我也许能为这个环境做出贡献。
记者:是什么吸引了您接受研究院的邀请?
贺子山:其实吸引力很小。 当研究生院发出邀请时,我可能最不可能接受。 我和我的妻子刚刚生了孩子,我们的其他孩子已经上高中了,他们不能离开。 这份工作意味着要住在北京,一个污染严重、交通拥堵、房间狭小的地方。 我的妻子留在加利福尼亚州,她说:“我们必须这样做。” 我的妻子不想让我失去这个机会。
其中涉及到很多琐碎的问题。 为了节省通勤时间,我睡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 我早上 5 点起床,通过 Skype 与女儿交流。 我还通过互联网辅导我的儿子。 我每两个月回加州看望他们一次。
记者:中国的教育是出了名的机械、僵化。 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贺子善:他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制度,因为过去运作得很好。
我理解为什么卡内基天文台是一个如此富有成效的天文学研究中心,在这里可以进行大量的自由讨论和集思广益。 我正在努力将这些实践带到我们中国的研究所。
我的梦想是,未来20年,哈佛、普林斯顿最优秀的学生愿意来北大,而不是北京大学。 我们研究所能做的就是提供一片绿洲,因为我对这片小区域有更大的控制权,所以我可以更快地让它成为现实。
我认为中国的制度是可以逐步改变的,卡夫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将进行平等互动讨论。 我们吸引了很多非常高水平的访客来授课。 卡维理研究所吸引了许多外国博士后来到这里,因为他们看到了这里的前景。 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在科学领域有很多投资,也愿意投资! 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基础天文学也只是一个业余爱好。 但在中国,他们愿意投资发展这门学科。 有了资金和这些优秀的人力资源,现在的关键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记者:经过一生的漂泊和劳作,您在北京找到了家的感觉吗?
贺子珊:我希望在这里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所以我努力工作,使这个项目取得成功。 我带着长期计划来到这里。 我正在学习说中文和写汉字。 有趣的是,我上次回去的时候居然错过了。 一年前,这里对我来说是最陌生的地方。